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2020年二级公立医院有四成出现亏损,而原因直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DRGS付费,文中还列出了医院、医生各种规避病种费用超支的措施,包括:分解住院、循环入院、院外购药等,标题甚至断言医保、医院、医生、患者4方麻将胜负已定。谁胜?无非是说医保是大赢家。
谁都不喜欢被监管,对于医保这道紧箍咒,医院和医生肯定是不欢迎的。但是为什么医保局要成立?欺诈骗保要督查?本人也感觉自己越来越不为医生同行所喜欢,因为我已经很少只从医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发出基于医生群体利益的质问,我越来越理性。
一、公立医院亏损是因为DRGS付费吗?
公立医院亏损真是因为按疾病诊断组付费(DRGS)吗?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按疾病诊断组付费(DRGS)设计原理。DRGS推行时病种费用测算都是按既往年度病种费用平均值测算的,这就意味着实施DRGS后就单个患者住院病种费用来讲必然会有节余的,也有超支的,只要保持既往收费结构不变,整个统筹区域内的病种总费用至少会保持不亏不赚。
那为什么网上总有文章说DRGS费用不够用呢?这里就有为利益发声的动机了。据我所知,很多公立医院都会对病种节余给予医生一定奖励,比例大多为10%左右,按理说有激励医生应该会有动力控费,那为啥关于DRGS费用超支的哀号一片呢?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医院管理层为增加节余罚大于奖或者只罚不奖。虽然从总额上讲节余会等于甚至大于超支,但是医院制定的对超支罚款额度往往远大于节余奖励力度,甚至有的医院超支有罚而节余却不奖,这是管理者为增收采取的一种不平等策略,导致临床医生总是被扣钱,而相应就会产生文章中规避DRGS费用超支十八般武艺。虽然医院某病种费用总额其实是节余的,但是由医生发出的信息似乎成了全面亏损,患者受折腾也被灌输是DRGS惹的祸,于是所有矛盾都集中指向DRGS付费本身,甚至医保局都被迫出面澄清DRGS付费对于住院日并没有限制。
二是医院对于医保节余的奖励比例小于药品耗材回扣比例。中国医改复杂之处在于医生是接受双重激励的:医院绩效与药品回扣。药品回扣由医生独享,而绩效往往会分到科室或团队二次分配,甚至有的医院只对DRGS超支有处罚,而对节余没有奖励,这就导致临床医生对于追求节余没有动力,有时甚至会算算大账,拿的灰色收入只要能超过扣款那超支也成了不错的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立医院亏损绝对不是仅仅因为DRGS付费,医生群体矛头直指按病种付费说白了就是想回归既往按项目付费老路,让医生开药用耗材没有限制,医保只按项目来买单。
二、公立医院亏损真正原因是什么?
从亏损定义来看,其实就是收不抵支,那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收入不足,二是支出过高。从现实来看,医疗费用年年涨相应医院毛收入水涨船高,医院仍然亏损只能说明其原因不在收入不足而在于支出过高,这就要从公立医院收入结构不合理说起。
看毛收入对于医院盈利能力没有太多实际意义,虽然医院尤其公立医院不该用利润率表述,但是为方便起见还是要借用经济学术语来分析一下医院的运营情况。在我国公立医院收入构成中,财政投入一般只占10%左右,也就是其余90%都要靠医院自己去创收,这就给医院亏损埋下了伏笔。下表是近年来财政投入在公立医院总收入中占比。

财政投入占比低,只能说明我国摒弃了市场化改革之前由财政完全兜底公立医院的公益医疗体制,并不一定意味着公立医院断奶后就会亏损,因为有一个地区公立医院就年年有节余,这就是三明。下表是三明公立医院2021年医师年薪发放情况表,我们不要盯着医师年薪具体金额,要关注薪酬总额从2011年3.82亿元增长到2021年19.56亿元。

三明早就已经实施DRGS付费,我们再来看看医保基金结余情况:


2012年是三明医改元年,而三明医改也正是在2010、2011年职工医保巨额亏空下倒逼出来的,从图中可以看出医改启动当年三明职工医保就实现了结余。那么三明地区如何做到医保基金年年结余,医院年薪总额年年增长?这就要看看公立医院收入结构。以下是全国公立医院收入构成结构图:

从中可以看出,2021年全国公立医院平均每100元总收入中,只有27元的医务性收入是纯收入,而在药品耗材零差率销售前提下56元药品耗材收入都是纯成本,不但没有任何增益,还要额外还要承担相应维护与损耗成本。再来看看三明地区数据:


由上图可见,三明地区公立医院纯医务收入由2011年3.1亿元增加到2021年15.20亿元,占比从改革前的18.37%,提高到43.05%(2021年全国平均水平仅27%);药品耗材费用仅从2011年10.15亿元增加到2021年10.7亿元,占比从改革前的60.08%,下降到30.39%(2021年全国平均水平高达56%)。下面我们测算一下假如三明不推进医改,各项费用会如何变化:
三明市2012年开始改革,二级以上医院(不含基层医疗机构),2011年医疗总费用16.9亿元(其中药品耗材费用10.2亿元,医务性收入6.7亿元),福建全省医疗费用2011年增长17.2%,2012年增长19.4%,2013年增长15.8%,2014年增长15.5%,三明如果不改革,按照全省增长中位数16%计算,数据分析如下:
(1)10年来医疗总费用按16%增长计算,要达到417.93亿元,实际268.04亿元,相对节约
149.89亿元(医保基金和老百姓减少支出);
(2)10年来药品耗材费用按16%增长计算,要达到251.08亿元,实际92.93亿元,相对节约158.15亿元。
(3)10年来医务性收入按16%增长计算,只能达到76.91亿元,而改革后实际达到103.3亿元,改革没有使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性收入减少,反而增加得利26.39亿元,比重从改革前的18.37%提高到现在的43.05%。
(4)另外,2014年全市22家县级以上医院首次转亏为盈结余1.2亿元开始,2015年结余0.79亿元、2016年结余1.54亿元、2017年结余1.07亿元、2018年结余1.8亿元、2019年结余2.36亿元、2020年结余2.65亿元,2021年结余2.69亿元,累计结余14.1亿元。同时,从2017年开始,医保基金结余打包奖励给各健康管护组织(总医院),累计13.58亿元。连同医院累计结余的14.1亿元,总共累计结余27.68亿元。
我们再来看看人均医疗总费用情况:

2021年全国人均医疗支出为5440元,而三明地区仅1877元,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三明地区公立医院健康发展并不是粗放式依靠收入总额增长,而是通过控制成本逐步优化收入结构来获得提升医务人员薪酬的改革红利。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其他地区公立医院大面积亏损并不是因为人群总医疗支出不足,更不是因为医保控费,而是没有很好控制支出成本,尤其是药品耗材支出,导致公立医院利润率太低。

相反,三明医改公立医院薪酬逐年提升,恰恰是通过减少药品耗材等成本支出实现的,三明用极低的人均医疗支出维持了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极低的人均医疗支出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医疗非常合理,浪费极少;二是人群健康水平高,这可以从上表中健康数据中得到验证。2021年三明地区人均预期寿命80.07岁(全国平均水平78.2岁)、婴儿死亡率2.33‰(全国平均水平5.0‰)、孕产妇死亡率10.13/10万(全国平均水平16.1/10万)。
三、医改需要消除过多内耗
那么三明是如何做到用极低的人均医疗支出支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三医联动改革。
通过药品耗材集中限价采购以及加强对不合理用药耗的监督,降低药品耗材单价与用量,节省出费用空间,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医保基金双打包(病种打包与总额打包)转化为公立医院提升薪酬的红利,用于推行目标年薪制改革,不断提升医务人员薪酬,再反过来让医务人员衷心支持改革、推进改革。
路径并不复杂,但是其他地区为什么很难做到呢?主要是因为医改缺乏统筹推进。三明地区三医联动改革是由政府层面来协同推进的,一把手挂帅医改,由一位分管领导统领三医。三明“腾笼换鸟”路径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性操作,改革者需要更多担当。
首先,推行药品耗材集中限价采购,打压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水分,必然会挤压乃到消除回扣空间,医生面临灰色收入眼前利益的损失,而腾笼换鸟目标年薪提升过程相对漫长,改革者在这段阳光替代灰色收入的过程中不但要面临医药代表的攻击,也可能面临医务人员不理解,这就需要极大的担当。
其次,三明医改初期还没有实行CDRG付费与医保基金总额打包,医保反哺公立医院主要是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实现的,而这绝对是一门技术活。为什么全国其他地区至今视公立医院呼吁良久的医疗服务价格提升为雷区,这是因为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但涉及医保基金能否承受,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增加老百姓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而全社会对看病贵已积怨已久,稍有差池可能引发社会群体事件。
三明的做法是稳中求进,只有在上一年度全地区医疗总费用增长低于10%的前提下,下一年度才考虑进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而且调整项目要普惠各家公立医院,幅度控制在医疗总费用增长不超过10%。而三明地区第一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则更具有技术含量。
三明紧紧抓住药品零差率改革来取消药品加成这一稍纵即逝改革机会,将由取消加成腾出的费用空间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采用价格平移的方式将其总额的85%转化为公立医院医务性收入,另外15%通过药品降价方式返利于患者。同时财政对于公立医院15%损失部分予以10%补偿。而在其它地区,因为没有抓住窗口期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导致取消加成的费用空间很快被药品价格上涨所挤占,不但未实现降低药价政策目标,反而助长了药品价格虚高,与零差率初衷南辕北辙。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医改需要大智慧。
三明三医联动改革经验已经很成熟,三明也在不遗余力传播改革经验,那其他地区就是学不来、学不好,原因在哪里?主要是因为缺乏超出部门利益的协同,医改要消除过多内耗。
公立医院由卫健主管,矛头就会直指医保控费,会痛斥医疗服务价格畸低,会整出分解住院、院外购药等损害患者利益的事2018年医改新政策,还会误导患者这是医保控费惹的祸来掩盖自身控费不力的事实,甚至把医院亏损的责任归结于按病种付费,却不知病种结余跟腾笼换鸟一样都可以用作提升医院薪酬总额的红利。
医保则只会紧盯公立医院过度医疗,而不愿主动去担当提升医疗服务价格,只想着控费来减轻医保基金超支风险,没有考虑公立医院实际困难,而按病种付费是不能完全替代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因为按病种付费仅限于住院,医疗服务价格提升还关乎门诊收入提升。有的地区医保甚至在公立医院有效控费导致病种费用下降时,下一年度直接下调相应病种费用标准,导致公立医院陷入控费成效越好收入越低的怪圈,最后公立医院干脆选择躺平不再积极控费,这样来年病种费用说不定还会上调。这种内耗的结果必然是改革推不动,医疗总费用年年高涨。
内耗最明显就是医保基金按人头年度打包给医共体(医联体)问题。在医保基金运转良好积余较多的地区,往往是医保部门贪恋手中的基金控制权,不愿意打包给公立医院。而有一些医保基金长期亏损地区,医共体又不愿意接手超支的医保基金。如果连医保基金都打包不了,如何能实现以健康为中心?
四、医改需要大格局
三明经验鲜明告诉世人,医改需要由政府层面统筹推进。医保、卫健、公立医院、财政等涉医部门利益是很难协同的,让这些部门主动提升格局是很困难也不现实的,只有由各级政府一把手统一挂帅,一位领导分管三医所有部门,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又离不开对政府履职考核。
只有将医改关键指标如:年度人均医疗总费用、年度人均药品耗材费用、年度人均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当年度人均预期寿命、群众满意度调查指数等纳入对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之中2018年医改新政策,作为一把手履职、提拔重要参考指标,产生由一把手推动、责任层层传递的改革压力,以此来推动改革。要将由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双组长)或其中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由一位政府负责同志统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作为医改组织指标监测体系之首。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医保、卫健、财政、公立医院等由局限于各自部门利益不能自拔的小格局,提升到团结协作推动医改步入以健康为中心的大格局。各部门在更上一层楼之后,医改大局面或许才能豁然开朗。

振兴乡村必须加快农村医疗体系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加...(147)人阅读时间:2023-10-27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深
甘肃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甘肃省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71)人阅读时间:2023-10-2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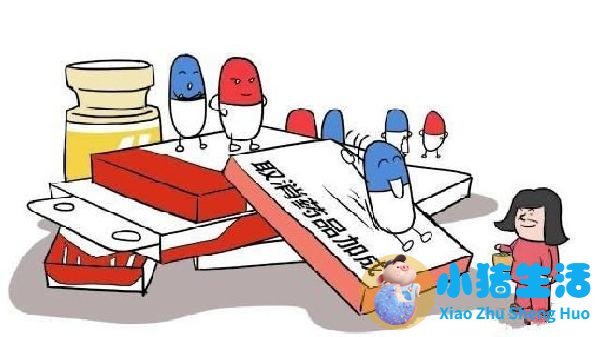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我国医改吹响攻坚号
全国所有公立医院已全部开展综合改革,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2017年4月,国家卫...(60)人阅读时间:2023-10-23
动态︱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我国医改吹响攻
全国所有公立医院已全部开展综合改革,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今年4月,国家卫...(88)人阅读时间:2023-10-22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药品加成必须取消
马海燕)中国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22日表示,公立医院改革,药品加成必须取消。孙志...(203)人阅读时间:202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