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可以订阅哦!



【引用本文】袁晓敏,曹 云,王 潇,等.肠道微生物术前准备与结直肠术后吻合口漏关系研究进展[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9,39(9):979-982.
肠道微生物术前准备与结直肠术后

吻合口漏关系研究进展
袁晓敏,曹 云,王 潇,汤 聪,陈玉根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9,39(9):979-98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No.)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江苏南京
通信作者:陈玉根,E-mail:
吻合口漏( leak,AL)是结直肠术后严重并发症,文献报道其发病率从3%~20%不等,而在低位结肠直肠或结肠肛管吻合术中AL发生率可高达24 %[1]。AL可导致严重的后果,如盆腔脓毒症、永久性造口的风险、全因病死率升高、病人生活质量下降、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资源消耗、癌症病人复发率的增加及长期存活率降低[2-3]。研究表明,结直肠术后AL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营养不良、手术方式、吻合口位置、吻合部位血供及术前辅助治疗等[4-5]。虽然吻合技术、诊断水平与术后监测取得了诸多进步,但在过去50年里,AL发生率与预后并未改善。因此,与技术无关的尚未被认知的因素日益受到关注。多项研究证实,肠道微生物在结直肠术后AL发生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将对肠道微生物与结直肠术后AL发生机制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通过现有证据,进一步讨论机械肠道准备和特定抗生素的应用是否有益于术后吻合口愈合,以期更全面地认识AL的发生机制,为临床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1 肠道微生物在AL 发病中的作用
60多年前的一项动物实验证明了肠道微生物在AL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6]。该研究首次描述了结肠吻合中的抗生素保护现象术前肠道准备方法,表明微生物很可能是吻合口漏的致病原因。几项前瞻性随机安慰剂盲试验,以及回顾性大型数据库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等[7]发现细菌在AL的病理生理学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提出管腔内容物和肠壁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在吻合口愈合的生理学中发挥作用。最近,van 等[8]对123例肠癌术后病人的研究中发现,当病人的微生物多样性较低时,其患肠AL的风险更高。然而,C型密封圈(用于保护吻合部位的管腔内片)的引入,几乎完全切断了肠道微生物与AL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些细胞水平上的研究使人们对肠吻合术的认识从单纯的技术层面转向了针对细胞和微观的研究,指导临床医生改进治疗思路,以减少肠AL的发生和可能与肠吻合失败相关的并发症。
1.1 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 肠管吻合后组织修复过程立即开始,这一连续的过程可被大体分为4个阶段:止血期、炎症期、增殖期及切口重塑期,肠道黏膜上皮屏障的修复是吻合口愈合中最核心的事件之一[9]。上皮屏障修复的受损导致黏膜下的组织层过度暴露于肠腔中的有害抗原(如细菌),可能代表AL发生的潜在早期环节。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host– ,HPI)可显著影响肠道微生物群,从而证实了这一过程在AL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正如的名言“没有酸,没有溃疡”,可以更好地表述为:幽门螺杆菌本身可能不足以引起消化性溃疡疾病,除非它发生在易感性宿主中[10]。即使细菌与上皮细胞的确发生相互作用,大多数吻合仍能成功愈合,这表明可能存在额外的损伤影响了吻合口愈合[11]。研究显示,宿主应激反应激活了应激诱导的细胞因子和激素,这些细胞因子和激素现在已被证明会改变微生物群和局部黏液屏障[12]。在临床实践中,肠道微生物的改变可能不仅仅是由手术应激引起的,而是整个围手术期管理的结果(机械性肠道准备、抗生素的使用、术前和术后饮食的改变、术后镇痛和阿片类药物、质子泵抑制剂或任何抑制胃酸药物的使用、经肛门引流管放置等),共生微生物会受到肠切除、吻合及围手术期处理等方面的影响,这导致了正常共生微生物群中出现更多破坏组织的菌种[13]。体内外的研究表明,宿主环境的改变可以诱导剧毒细菌的活化进而导致组织损伤。这可以解释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何破坏肠道吻合的愈合[14-15]。在吻合部位发生的HPI对上皮屏障的重建产生显著的破坏作用,这可能解释病原微生物如何促进AL的发生[8],等[16]发现模拟辐射效应可能会改变特定细菌的毒性表型,术前辐射可将铜绿假单胞菌诱导转化为吻合破坏表型,表现为胶原酶活性增强、高群集运动性和对肠上皮细胞的破坏,并与大鼠模型术后的AL的发生有关。细菌造成的肠上皮细胞死亡和肠屏障破坏,可能是产生术后吻合失败的必要因素。
1.2 基质金属蛋白酶产生菌 研究表明,某些细菌的作用似与肠AL的风险增加相关。等[13]发现,具有高胶原酶活性的剧毒细菌可能会导致AL的发生。他们后续对大鼠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粪肠球菌通过其胶原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激活功能导致AL,这表明肠道微生物中可能存在漏表型细菌。基于菌株的胶原降解活性及宿主MMP9激活能力,漏表型细菌可分解肠道组织中的胶原蛋白,从而导致AL。在大鼠模型中注射头孢西丁没有杀死粪肠球菌,也未阻止AL的发生。而对从人体吻合组织中分离的64株细菌的初步调查表明,只有铜绿假单胞菌和粪肠球菌表达胶原降解/MMP9表型。MMP的重要性及其在吻合完整性中的作用进一步在人群研究中得到验证,该系列研究发现结肠吻合口周围的组织含有大量MMP,进一步的胶原分解可能破坏组织完整性,从而导致AL的发生,而施用MMP抑制剂可改善术后吻合的组织强度和组织完整性。因此,某些MMP及优先分泌MMP的细菌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以防止它们的有害影响并减少术后AL的发生。
1.3 丁酸产生菌 尽管临床医生通常认为肠道细菌是吻合口愈合的障碍,但切口附近存在的微生物群也可能有积极的影响。微生物群的某些常见成分,特别是丁酸产生菌,已被证实有助于上皮修复[17]。结肠腔内的细菌将可溶性纤维发酵成短链脂肪酸和其他具有潜在益处的代谢物。丁酸()是一种重要的短链脂肪酸,负责细胞增殖,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这种细菌代谢物对于支持上皮细胞的生存能力和屏障完整性非常重要,且能下调促炎细胞因子[18]。在大鼠模型中,左半结肠切除吻合术后给予丁酸盐灌肠剂增强了吻合口的强度,这可能是由于促进了胶原合成和成熟。丁酸盐及其母体复合纤维也可能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通过增加肠腔内容物的机械性运动及加速结肠运输,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结肠上皮暴露于肠腔内有害抗原的机会。
1.4 粪便稠度对微生物结构的影响 粪便稠度和流速也被发现与肠道微生物群和吻合愈合有关,因为微生物含量最有可能受到细菌的生长速度和黏附肠黏膜层的能力的影响[19]。最近一项纳入277名健康人群的临床研究表明,除年龄和性别外,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根据性状将大便进行分类的方法,可反映结肠运输时间)是影响肠道菌群结构的重要因素[20]。而在直肠癌低位前切除(LAR)术后的病人中,术后早期腹泻与排粪量被证实与AL发生相关,直肠癌LAR术后早期腹泻可作为吻合口漏的预警信号,术后3 d粪便量≥110 mL可能是AL的可靠预测指标[21]。术前机械性肠道准备、术后结直肠功能受损、结直肠癌术后辅助放化疗等常使经历结直肠手术的病人排便次数、排便稠度发生明显改变,进一步导致肠道微生物构成紊乱,可能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术后AL的发生。
2 术前肠道准备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术前肠道准备包括机械性肠道准备( bowel ,MBP)和抗生素肠道准备( bowel prep⁃,ABP)两部分。关于术前肠道准备,在普通外科和结直肠外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2.1 机械性肠道准备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长期以来,MBP被认为是外科手术的教条,目前仍被多数结直肠外科医生使用。MBP在择期结直肠手术前进行,以大量减少肠内容物,这是结直肠渗漏和感染病原体的来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部位感染(SSI)的机会。除了所谓的“肠道清洁”的传统效果之外,其他技术因素也指出了在外科手术之前使用MBP的优点。近年来,由于MBP在众多临床试验中一直未能显示出对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独立保护作用,MBP的使用率有所下降。除对于需要低位结肠肛管吻合术的直肠手术外,许多专家倾向于术前不对病人进行肠道准备。在2015年美国公布的3项大型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BP联合口服抗生素显著改善了结直肠切除术的结局,人们开始重新认识MBP的重要性[22-24]。这种联合将结直肠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了近一半,包括手术部位感染、AL和肠梗阻。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近期,Vo等[25]同样发现,对于接受择期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切除术的病人,口服抗生素和MBP的联合使用会显著降低SSIs的发生率。这些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肠道微生物群在吻合口修复方面的重要作用。
2.2 机械肠道准备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肠道清洁产品的灌洗对结肠微生物群的影响到迄今尚无确切结论。聚乙二醇(PEG)溶液因容易给药、更舒适、病人接受度高、并发症少在临床应用广泛。然而,PEG溶液会导致肠道正常黏液的中重度流失,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摄入的PEG电解质溶液会排出管腔内细菌,将氧气引入通常厌氧的结肠生态系统,并会减少肠道细菌的营养供应。这些变化可能会迅速破坏肠道微生态系统。此外,MBP不会“净化胃肠道”,因为细菌数量与不进行MBP时几乎相同。MBP扰乱肠道微生物群结构,降低微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允许机会性病原体茁壮成长[26]。结直肠术后病人的菌群紊乱甚至长达几个月仍无法恢复,相反,在健康受试者中,在MBP后几周,微生物群组成几乎完全恢复正常。所有描述MBP后肠道微生物群变化的研究都显示了明显的微生物群结构紊乱和多样性减少,但尚无法确定具体模式。最常见的情况是变形杆菌和拟杆菌的数量增加,乳酸菌数量显著减少,肠杆菌家族数量增加,革兰阳性和阴性物种比例的急剧变化,氧气的进入通常导致变形杆菌数量增加。此外,pH值的增加可能会减少特定细菌代谢物(如SCFA)的损失,从而利于变形杆菌的繁殖。
这些不断发展的理念可能为设计更有针对性的肠道准备方案提供参考,以降低术后吻合口并发症的发生。有研究指出,含有营养物和抗气胀剂的“肠道准备2.0”的平衡溶液通过产生更加平衡、多样化的微生物群,对黏膜上皮和黏膜下免疫细胞产生有益的影响,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更科学有效的外科肠道准备方法,既可保证肠道清洁,同时又能保持正常微生物群的重要功能[27]。
2.3 抗生素的使用对肠吻合口愈合的影响 除上文提到的关于抗生素与机械肠道准备的联合应用,还有多项临床研究证实抗生素的单独使用对预防术后AL可起到保护作用,近期一项包含2691例行低位前切除术的直肠癌病人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术前未能给予口服抗生素是AL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8]。另一项回顾性研究甚至发现与单独口服抗生素相比,口服抗生素和机械肠道准备的联合方案在减少手术部位感染、AL、术后肠梗阻方面没有优势[29]。然而,并非所有常用的口服抗生素都有积极作用[30]。已经发现诱导细菌易位的抗生素在对抗上皮损伤的同时也会导致炎性反应增加[31]。与MBP相反,非必要的广谱抗生素会对微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和持久的影响,抗生素制剂导致细菌总数下降,虽然之后细菌总数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是多样性的再生非常缓慢、不完全(甚至在几个月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后果。
肠道准备,无论是否应用抗生素,都会扰乱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及平衡,从而影响吻合口的愈合过程[32]。因此,抗生素应用的预期益处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尽管抗生素存在预防术后并发症与微生物群干扰的双重作用术前肠道准备方法,但尚无其他替代药物被证实可应用于临床。
3 总结与展望
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对人体的健康起着重要作用。人们越来越关注肠道微生物在吻合口愈合中的有益及病理作用,这两方面很可能是未来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然而,AL复杂的、多因素的病理生理学机制至今仍未完全阐明,有关于微生物的作用,对其认识还停留在起步阶段,迄今为止获得的结果仍然过于描述性,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充分理解肠道内菌群之间的特殊相互作用及其在切口愈合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迄今为止,对于是否应该在外科手术之前进行肠道准备,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应努力寻找有针对性的方法,确保能够选择性地抑制致病微生物,同时保存有益的细菌。这种针对性的术前治疗将创造最佳的肠道微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微生物群的特定管理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如何有针对性地使用新一代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元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研究领域[33]。
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的普及,使得人类对肠道微生物的认识已深入到菌种、功能基因等层面,临床医生应脱离经验主义的束缚,在临床实践中尝试利用基因测序来控制微生物群对手术结果的影响,以减少AL、手术部位感染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略)
(2019-05-04收稿 2019-06-23修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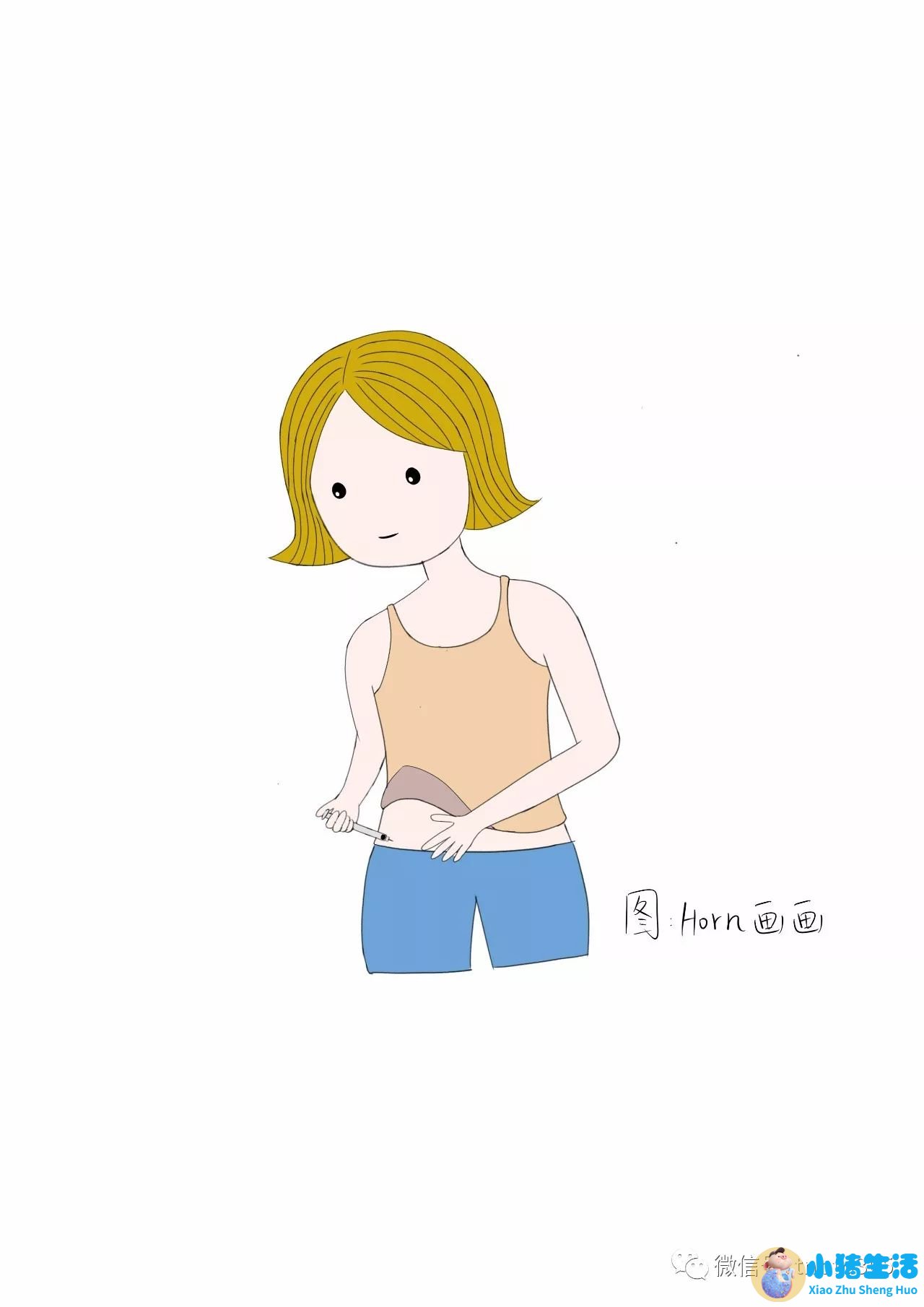
究竟哪些人需要使用胰岛素治疗?
所以通过口服降糖血糖不达标的患者,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启用胰岛素治疗方案。胰岛素强化...(136)人阅读时间:2023-10-26
胰岛素的副作用盘点,知己知彼方可百战
我们一直在强调胰岛素带给人类的巨大贡献,到目前为止,胰岛素是治疗1型糖尿病的最主要药...(174)人阅读时间:2023-10-26
眼睛做激光手术的适应症
眼睛做激光手术的适应症1眼睛做激光手术的适应症疑惑二、哪些人都做通过近视手术恢复视力...(56)人阅读时间:2023-10-2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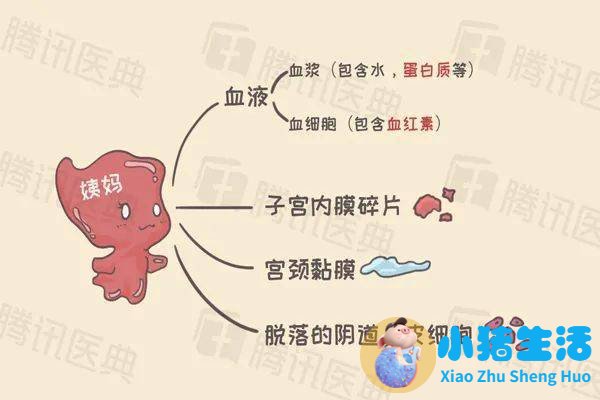
月经推迟小腹疼痛是什么原因,月经量突然
每一个正常女性在每一个月都是会经历月经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但是,对于不少的...(144)人阅读时间:2023-10-20
更年期故事:左下腹胀5年,消化道症状怎
有人或许好奇,这下腹胀明明是胃肠道症状,不去消化科看医生,却去看更年期和月经病为主...(188)人阅读时间:2023-10-10